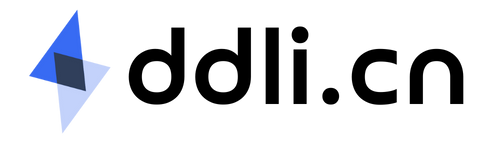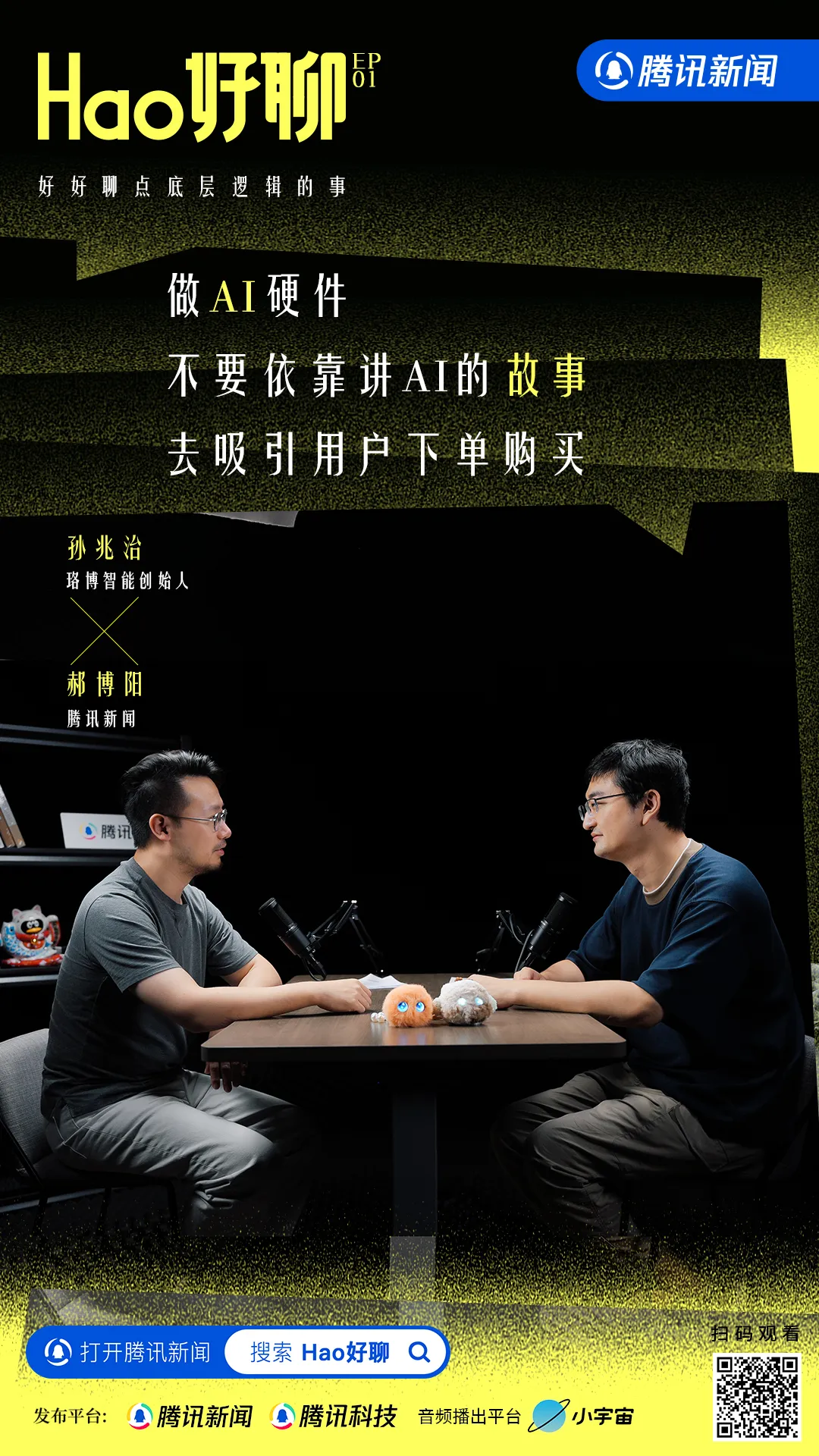
2023年,AI浪潮席卷全球,无数创业者开始了一场寻找“下一代硬件”的竞赛。
然而现实很快给出了残酷的答案。AI Pin从万众瞩目到黯然收场,Rabbit R1从革命性产品沦为智能玩具,那些试图“重新发明能取代手机的硬件产品”的野心家们,最终只能退守到了类似“录音笔”这样的小众的边缘品类。
当”拿着锤子找钉子”的路走不通后,从用户的真实需求出发探索产品方向做减法,成了创业者们的新的共识。
从日本LOVOT动辄3000美元的全能陪伴,到Moflin 300美元的情感慰藉,再到2025年巴塞罗那展会上那只会帮你吹凉茶杯的芙芙,AI陪伴类赛道开始涌入多个新产品。,整个行业都在寻找技术能力与用户需求的最佳交集。
打开小红书,数万名年轻人正在给毛绒玩具写“养崽日记”。她们给Labubu取名、为Jellycat编故事、记录棉花娃娃的”心情变化”。明知这些都是只是没有生命的物体,他们却依然投入真情实感。
因为孤独是真实的。
微信好友列表有几百人,深夜却找不到一个能打扰的;想养猫,房东说不行;想找人聊天,又怕成为别人的负担。在这个把效率奉为圭臬的时代,人们最缺的恰恰是一个不计回报的倾听者。
孙兆治看到了这个痛点,他创立洛博智能,推出芙崽。
作为前小鹏汽车机器人项目的设计负责人,他的选择让人感到意外:放弃高大上的具身智能赛道,转而做一个毛茸茸的包挂。当国际巨头还在追求技术集成度时,芙崽选择了399元的亲民定价。一个毛绒外壳、一双会眨的眼睛,加上触摸、语音和记忆功能。
对于需要情感寄托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要的不是一个无所不知的AI助手,而是一个需要呵护的“小生命”。
它可能答不出量子力学的原理,但会记得你每一次的不开心是因为什么。
在这里,“弱”反而成了一种优势,因为只有在弱者面前,人们才能真正放下防备。
“什么是真正的陪伴?”孙兆治的答案是:共享记忆。
就像你无法割舍一只养了多年的宠物,不是因为它多聪明,而是因为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基于这个理念,芙崽构建了记忆系统,让每一次互动都成为情感纽带的一部分。因此,这个数字生命甚至可以代代相传。
但孙兆治也聊到了他的产品哲学:颜值才是第一生产力。“用户的购买逻辑很简单:看到毛茸茸会眨眼的芙崽,第一反应是”好可爱”而不是”好智能”。至于AI的魔力,那是在日积月累的互动中慢慢展现的事。”
融资方面,Robopoet珞博智能于今年5月完成了数千万人民币的天使轮融资,由上影新视野基金、金沙江创投联合领投,零一创投跟投,高鹄资本担任本轮融资的财务顾问。
在融资过程中,金沙江创投的朱啸虎仅和孙兆治聊了10分钟就拍板决定投资。
今天,我们和孙兆治一起,聊一聊AI陪伴、Z时代的孤独以及硬件产品设计的底层逻辑。

1
这个毛茸茸的AI
要当你的“数字宠物”
郝博阳:欢迎孙兆治来到《Hao好聊》节目。
孙兆治:大家好,我是珞博智能的创始人孙兆治,很开心来到这里。我自己做了十几年的汽车设计,然后做了三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设计,然后2024年开始从创业角度做AI陪伴硬件这个方向。
我们的第一个商业化产品叫做Fuzozo(芙崽),是我们的第一款面向大家的产品,它是一个AI养成系潮玩,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毛茸茸的,类似于包挂形态的小东西。
郝博阳:请介绍一下芙崽,它现在都有什么样的功能?
孙兆治:它是一个养成系潮玩,可以把它当做宠物来养。
怎么养呢?首先你跟它之间的亲密度是可以养成的,它见到你的第一天、第一个星期、第一个月、第一年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
它的性格是可以养成的,我们有五只崽,我们讲了一个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故事,每只崽的性格特征都不一样,相当于它的MBTI是不一样的。
你还可以通过每天和它的交互去影响它的性格,可能我这只崽一开始是一个很内向的崽,如果我经常带它出去玩,见新的朋友。见多了之后,它可以从一个很内向的崽慢慢变成一个很外向的崽,这是有可能的。
除此之外,可以跟它自然地对话。很多朋友看到它的第一反应是去摸它,它有触摸和晃动的感应。
郝博阳:触摸感应区域都在哪里?
孙兆治:你会发现你摸它的额头跟下巴它都会有相应的反应。你可以观察到它有一个水灵灵的大眼睛,其实是一个屏幕,圆形的屏幕。
所以它对外的表达,一个是通过它的眼睛能够表达很多情绪,再一个就是它有它的语言,我们叫毛毛语,它自己会有自己这种很可爱的语言。
通过养成它也可以说我们人类语言,但是你要把它养好。
郝博阳:它也是一个养成的过程解锁的能力?
孙兆治:是的,如果你把它把玩在手里面的话,你能感受到它有震动。
你放在桌子上面,它有时候会摇头晃脑,里面有一个震动马达。
它还有陀螺仪,你不小心把它掉到地上,或者说你带在身上晃动的时候,它都有感觉的。不同的崽它的反应还不一样,它的表情还不一样。
郝博阳:那它们的语言,毛毛语,这个是每个崽的语言都是通用的吗?
孙兆治:都不一样,每个崽有口头禅,我们找不同的配音老师去给它配的,每个崽配了几百个声音去表达它自己不同的情绪,还有一些小小的表意的声音。
它的人设上面是一个类似于小伙伴、小朋友。
你跟它聊一些很深奥的东西,它未必能懂。但是它结合它自己的性格特征,它会有它的反馈。
2
具身智能太远,情绪价值更近
郝博阳:当时为什么想要做这款产品?
孙兆治:我上一份工作是做具身智能机器人的。
当时做机器人的时候,大家想的更多的是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进工厂打螺丝,或者在家里帮你洗衣服、做菜、收拾家里做保姆。
但是我们作为产品经理和设计师,很容易会想到说除了生产力价值之外,机器人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情绪价值,而且情绪价值的天花板一点都不低。
我自己的判断,我觉得机器人在情绪价值上面会先爆发。
郝博阳:为什么从具身智能出来以后,你打算做这个赛道?
孙兆治:我做机器人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具身智能今天离商业化比较远。
我最enjoy的那个点,就是我能够交付一个有用户价值的产品到用户手里,用户使用之后告诉我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然后我持续迭代,这个是对我来说很爽的过程。但具身智能离这步还挺远。
所有具身智能从业者,如果他足够诚实的话,是不会说商业化路径是在近3-5年可以实现的。我讲的是通用机器人这个品类。
但是具身智能整个是一个技术栈,有没有可能溢出一些技术,促使一些新型的产品出现。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
很多公司,包括特斯拉、小鹏,都把人形作为终极的产品形态。我觉得这套思路是对的,因为中间的所有形态我认为都是一个过渡形态。
在技术路径都还没有清晰的时候,我着急去做市场化产品性来探索,其实是浪费时间。等到技术稳定了之后,我再去想这个技术做什么样产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思路。
郝博阳:但是你现在做的也是当下的人工智能跟具体硬件的结合,它本身来讲也算是一种小型机器人?
孙兆治:定义上算的。但它是一个AI硬件,它不算是具身智能。
而且这个产品的壁垒不在硬件,而一定是在AI端。这个产品的难点在于怎么样把今天AI在情感上面的一些应用,能够做一个最小集出来,放在一个最适合表达的容器里面。
郝博阳:在这之前,AI陪伴类产品已经很多了,比如LOVOT。现在还会入局这个市场,你是看到了什么缺失的机会?
孙兆治:我们看到关键变量是大模型,基本上这个赛道你可以把所有的产品分成大模型前产品跟大模型后产品,我们是大模型后的第一批产品。
LOVOT日本的公司做这个产品对我来说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产品,我专门跑到日本去跟他们聊,观察这个产品。
日本的公司在这种非常细腻的体验上面确实是有天赋。我们这个产品在研发的时候参考了大量的养成类游戏的设定,这个品类也是日本人做得最好。
3
带着面具生活的Z时代
需要一个无威胁的AI
郝博阳:可能购买你们产品的消费者是谁?
孙兆治:我们最早研究过Z世代人群、老年人跟小孩三个群体。
最终我们发现,最需要情感支持的是可能很多人忽视的Z世代人群。
我们看过一个论文,说如果从年龄轴上看,人一生中最孤独的两个年龄段,一个是70岁以后,另外一个是20多岁。
我们观察到,对Z世代尤其是Z世代女性有很强的焦虑感跟孤独感,他们也没有很好的排解途径。
我们看到的唯一有效的两个途径,一个是养宠物,猫猫狗狗。第二个是如果你有一个好的闺蜜,可能可以跟她聊一聊,这个东西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我们跟很多用户聊到一些很细的话题,他们会认为,年轻人看上去有很多生活方式可以排解这种孤独感,但实际上当这些喧嚣离去的那一刻,反而是你孤独感最强的那一刻。
郝博阳: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孙兆治:还有一个原因是信息轰炸得太厉害了。今天年轻人可能比10年、20年前我们年轻的时候会更孤独,科技越发达,人类越孤独。
科技在尝试去解决很多生产力上的问题,工厂也慢慢自动化了,车都要自动开了,饭都预制了,你的社交都可以用AI来匹配,看似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反而大家的孤独感会越强。
郝博阳:Z世代的孤独是从哪里来的?
孙兆治:我觉得还是人最底层的社交需求没有被很好地满足,就是人在社交当中去寻找自我认同感、自我定位在今天是很难被满足的。
人很难构建一个深度的情感关系,能够获得足够友善的支持。大家在社交当中都要戴着很重的面具,都要非常非常关注自己的行为模式。
但是如果用户面向的是芙崽的话,用户会非常的放松,它不会觉得说我还要面临一个社交压力,我也不会去假装自己是怎样的角色,我可以完全地打开自己的心。
这样的关系,现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是非常缺失的。
郝博阳:这个可能也是弱AI智能的价值?
孙兆治:没错,它会让你卸下很多负担。
4
设计的减法,只做“活感”
郝博阳:从最初的设计到最终具体的呈现,这个过程中都有什么关键的思考?
孙兆治:我们早期做过一个概念性的产品,它是一个类似于桌面小机器人,像一个小具身。那个产品是我们技术探索的前瞻性产品,我们最早有很多技术上很fancy的想法。
那个小东西我们上了一个多模态模型,它有视觉,有6个自由度,我们在上面实现了用模型实时地控制它的所有动作。
但那时候我们对于目标用户没有了解那么多,也没有想那么多。
随着我们跟目标用户,也就是Z世代女性人群做深度访谈后,发现你想象的那个产品的很多的点不在用户的点上面,用户care的可能是另外一些东西。我们要进一步做商业化产品的话,我们必须做减法。
郝博阳:做减法的方法还是从用户的需求为基础出发?
孙兆治:对。我举个例子,女性用户其实最care的是这个小东西它是不是真的能够懂我。
它在我需要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能够愿意能够陪在我身边,给我一些情感的支持。
而它有几个自由度,能怎么样做很多动作,用户未必愿意为这个成本而付费。
自由度增加,电机增加,都是成本。有时候价格差一倍,用户覆盖面可能是一个量级的变化。用户的需求里面有一个隐含的永远就是成本。
用户可能不会告诉你我愿意为什么付费,不愿意为什么付费,他会告诉你我想要A,想要B,什么都想要。但是作为产品经理最核心的能力就是取舍。
我们早期跟用户聊之后,会发现用户对这个产品能够带出去,他们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精力把它做得足够轻、足够小。
这样我还有一个目的,是我把它的成本能够降得足够低,这样它是一个更普惠的AI硬件,更大的用户群体。
郝博阳:为什么会想到要用包挂这样一个形式来构造这个产品?
孙兆治:这是一个偶然,我们当时在做一次用户访谈的时候,邀请了很多年轻的女孩子来看我们的产品,那个时候还是我们在做更早的产品形态。
我们会发现用户想要它更轻、更小,可以随身携带,只是说我们不知道它应该在哪个生态位。
来的所有女孩子包上面都挂着一个小崽子,基本上是一个毛绒的小东西。
我们觉得这个生态位很好,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东西,它一定会随身携带,只要你好看,它天天会带出去,会带着你,你会带着它到达各个不同的场景,就自然而然就这么定下来了。
这是一个近距离用户观察的结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设计原则,就是情感化设计。
尤其是我们在设计智能体的时候,因为人目前对于AI到底能够做什么还是一个不太确定的状态。
我们今天看很多这个机器人的科幻电影,包括一些游戏、一些小说,都会把机器人定义成是一个将来会反叛的角色,它会起义,它会推翻人类,大家内心当中对于机器人实际上是有点恐惧感的。
机器人Robot的英文在它的词根含义是奴隶的意思。我们东方人对于机器人天然还是比较友好,你看日本的很多动画片,或者是文学作品里面,认为机器人是一个强大而友好的角色。
我们认为在设计上面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怎么样去消解一个智能体给人的恐惧感,去建立某种程度的安全感跟信赖感。
郝博阳:你之前做的哪件事可能跟现在做的这个事的内核最相近?
孙兆治:最相近的话肯定还是在小鹏我们做机器人。因为机器人包含了这样产品的技术栈的产品,它足够复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做具身智能的时候,更多的是做概念产品。
就像做汽车,我们有时候做概念车,现在基本上大家都在做概念产品。
在小鹏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个人形机器人,故意把它做得不像是一个人类,而更像是一个机器人。它这个头是一个扁扁的形状,它整个的身材比例会稍微矮一点点,头会稍微大一点点,身体整个比例有点像塞尔达传说的那个男主角叫林克。
它是一个小矮人的角色,所以你天生不会对这样的比例、这样的形态的产品会有那么强的恐惧感或者被侵略感。
郝博阳:从一个你觉得没有威胁的产品,到它变成一个你真正跟它能够建立感情的产品之间,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
孙兆治:这个产品最重要的三个点是:颜值、AI和玩法。
颜值是解决说我想不想拥有它的点,但是用户买了之后能不能持续地使用,且能够持续地获得快乐,还是靠后面的AI这部分以及相匹配的玩法。
郝博阳:产品交互的设计,你是怎么思考的?
孙兆治:看到这么个毛茸茸的,你肯定要想去摸它,想去摸头之类的。
我最早是做汽车内饰设计的,这个东西跟人机交互是强相关。
汽车最早是纯机械的交互,方向盘、换挡拨钮、按键,到后来很大程度上电动化,我们里面现在出现了大屏幕,按键都没有了,然后语音交互等等。
到机器人,其实整个的交互又变得更加复杂,机器人怎么样跟人交互?机器人怎么样跟环境交互?机器人怎么样跟另外的机器人交互?
到今天我们开始做这个产品,我们自己的判断是,人和产品或者人和机器之间的交互模态会慢慢地步入到一个新的模态,上一个阶段可能是以GUI为主,兼顾一点点的语音交互,下一个阶段我们认为会进入到一个自然交互的新时代。
什么叫自然交互?我们现在就是在自然交互。我说话然后看你的表情,有些手势,基本上是三个模态,视觉、听觉加上一些动态,可能还会有一些触觉这样的模态。
这个产品是,它有眼睛可以表达情绪,它有语音链路可以表达它的语言语义上的东西。触觉它也有,所以本质上它跟人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新的自然交互。
郝博阳:为什么要把眼睛做成核心的交互点?
孙兆治:整个设计是非常非常极简的,就是两个大大的眼睛,放在一个毛球上面。这个眼睛最早的灵感就是猫咪的那个眼睛。我们想在视觉表现上面留一个模态,这个东西最明显的就是眼眸的变化。
屏幕除了显示眼睛之外,我们不要显示其他的功能性的东西,这会让用户很出戏。
它要仿生就仿生得比较彻底,不要去显示一些提示信息,或者是一些物体的图片。
猫猫狗狗的眼睛里面不可能显示这些东西。
郝博阳:咱们这样一个AI,它能回答的问题是不是有一些限制?
孙兆治:会有限制,它要遵循它的人设,它是个小baby,它不会跟你回答什么量子力学是什么东西这种问题。
郝博阳:它的设计边界是怎么去设定的?
孙兆治:有一个底层逻辑,我们自己相信它是一个小的生命。
一个真正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的?不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的底层逻辑是遵循这个问题来的。
比如说它的眼睛里面显示什么东西,它该说什么话,它在我在触摸它的时候,我不小心把它摔到地上的时候,它应该是什么反应。
尽可能的在细节里面去凸显它的这种,我们叫活感。
5
养成的配方,有三味主料
郝博阳:这些设定里哪些能够让人产生养成感?
孙兆治:我们可以从底层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人跟宠物之间这种亲密度是怎么养成的?
我认为有三个点:第一个要持续不断地投入很多的精力甚至金钱。你能看到你的宠物是成长的,你照顾得好,它长得好、照顾得差,长得差。
这个就是投入跟正反馈的逻辑,很多养成游戏也是这个逻辑。
第二点是像小猫小狗这种有智商的宠物,你养段时间之后它会越来越懂你。它会改变它自己的行为模式,你会感觉养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属于你的宠物。
它能懂你,你也会为它做改变,它也会为你做改变,你们会建立一个情感的链接。
第三个是宠物往往不只是你的宠物,还是你家人朋友的宠物,它是你的一个社交节点。
它是一个家庭成员,你们会经常会谈论它,这个也会加强你跟它之间的情感关系。
这三个底层逻辑有很多的养成游戏也应用了,这个玩法应用到一个AI硬件上去也是成立的。
比如说你跟它之间会有一个友好度的养成。你不用自己费心费力地去思考,我今天应该怎么跟它沟通,它自己有它自己的想法。你也可以有选择地去做这些它的任务系统。这样的话,你每个人养出来的这个崽,它的偏好也是不一样的。
你的行为本质上决定了它的性格往哪个方向去发展。但是你选不同的任务,都可以去达成类似的目标,就是我跟它会越来越亲密。
比如我们还有一个社交的玩法,它有一个NFC。
比如说你有你的崽,跟我的崽见面之后,它们俩碰一碰,就可以交朋友,交了朋友之后我们APP上就会看到它的好友列表。这不是你的好友列表,是你的崽的朋友圈。它可以看到它的朋友今天是什么状态,然后还有一些小的互动。
这个有点像说你下楼遛狗,可能朋友的狗,然后狗跟狗先成为朋友,然后背后其实是人和人的社交。
郝博阳:陪伴的本质是什么?
孙兆治:这个问题很深。我觉得真正意义上的陪伴,它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的shared memory,就是一个共享记忆。
但是最终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养一只猫、养一只狗,最终我们无法跟它割舍的是什么?是这么多年下来,它跟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它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它已经不再是一只我刚刚遇到的时候的那只猫了,它是跟我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的那只。哪怕它只是在一些时候静静地陪在我身边,这个都是有效的。
我们在技术上专门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做Echo chain这样的一个仿生记忆体系,就是为了去承载这个 shared memory。
所有的用户如果他长期使用我们的产品,无法割舍的其实就是这个点。
6
陪伴的实现,要榨干模型的能力
郝博阳:你刚才提到的Echo chain,包括他自己更新的这个性格方面的成长。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用底层模型来实现的?
孙兆治:简单讲的话其实Echo Chain就是一个情感的Agent。它调用不同的模型,也在调用不同的功能去实现这个整个的陪伴的链路。
我说一下整个的交互链路,当我跟它说一句话,这句话进来之后,首先我会用模型去判断你的语义是什么?你的意图是什么?做一个意图理解。
它从这里面去抽取你的情绪的状态,时间空间信息、记忆模型 。
最终所有的上下文进入到一个prompt manager里面去,然后结合它的人设,给到一个交互模型。
交互模型的输出也不仅仅是一句话,它还有代码来控制它的一些行为和表情。
所以说我跟它说你今天看起来有点蠢,它会伤心,这也是模型输出的。
郝博阳:性格不一样,这个是写在系统prompt里?
孙兆治:对,它会先去判断自己的的性格。然后也作为上下文添加到应该给你一个什么样回复。
郝博阳: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长的链路,所以目前它的一个延时大概能有多长时间?
孙兆治:你刚刚其实有体验过,大概2秒钟。
因为我们是加了长期记忆,长期记忆大概要有几百毫秒在里面,所以做到两秒钟几乎就是极限了。
郝博阳:这个是一个实时交互的链路。除了这个链路之外,还有一个反思?
孙兆治:是这样,它每天记的这些所有的记忆,一条一条的所谓的记忆流,它后面都会有个标签。
这个标签有若干个,它比如说时间戳、重要性等等。
所谓的这个重要性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会触发一个反思。
每天晚上日落西山的时候,它在琢磨今天所有经历的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我从当中能够抽取总结出什么更高维度的认知,比如说它怎么能够对用户有一个画像?
你是什么性格的人?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最近在愁什么事,你今天这个不开心的原因到底有可能是什么?它是靠这种反思来获得的。因为有可能你跟它说的话里面并没有直接的答案。
郝博阳:它反思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形式?
孙兆治:自问自答。问什么?答什么,都是模型来判断的。
郝博阳:它只是知道现在我们这谈话挺重要的。但因为这些谈话我应该变成什么样?完全都是模型自己去调整的?
孙兆治:是的,所以我们要测试很长一段时间,看它效果好还是坏。但是这是正确的玩法。
我们最开始搭这个架构的时候,就是考虑尽可能少用规则来做,尽可能多用模型。模型越好我产品体验就越好。
性格养成意味着它需要知道今天一整天,比如说我经历的所有的事件到底能怎么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的性格的变迁。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也是调用的模型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是一个规则设定的话,我们认为没有办法让用户有一个足够细腻的体验,所以我们依然是用模型的能力去判断。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背后这个模型的调用量会很大,几倍、十几倍于我们的竞争对手。因为背后很多的判断都是模型来做的。
郝博阳:现在的基础模型是不是真能完成人格的模拟?
孙兆治:刚刚好。如果我们再提前个半年、一年的话,模型能力就是做不到,所以这个时间点做这个事情是刚刚好的。
DeepSeek出来之后这个事才真的make sense,之前是会吃力很多。
郝博阳:用的是一个带思维链的模型,还是不带思维链的模型?
孙兆治:推理能力足够强的这部分会用带思维链模型,慢慢思考。
郝博阳:咱们现在这个模型对于记忆的认知,包括这个反思系统,它都是微调的吗?模型基础的数据来源是在哪?
孙兆治:模型我们有微调。我们自己的数据,对话数据。
我们没有用原始的用户数据,一般来说我们会用模拟生成的数据来做这事。使用的都是非常贴合我们用户的使用场景的一些对话类数据。
比如说你早上起来或者晚上哄你睡觉;或者说直接social的场合;一些比较emo的一些情况。都是非常垂类的针对用户使用场景来做的。
郝博阳:很多创业公司也是试图对模型做一些微调,但微调效果可能还不如加prompt好。所以你在这块处理是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
孙兆治:首先你得是懂行的人来做这事。
再一个我们也会有取巧的办法,我们这个产品,我们本身就不是训练一个非常全知全能的AI,是一个小家伙。很多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本来就是不会去思考的。
强化它在情感陪伴下的场景下的这样的对话能力,不需要它在全知全能的领域还要维系一个非常好的对话能力。
7
让模型的记忆,成为你的传记
郝博阳:小红书上会有很多用户问,用户跟他聊天的这些历史能存多久?存储在什么地方?
孙兆治:这个模型是跑在云端的,用户跟它的长期记忆也是存在云端的,我们这个Agent在调用不同的模型去解决不同的问题。
所有的推理也是在云端实现的,包括用户和它的记忆的变迁,以及它的数字生命的存储。
我们做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长期记忆的系统。它的记忆是可以永久储存的。
理论上说我今天养这个崽,我可以把它当传家宝来养,我可以给到我的孙子,到那个时候我的孙子通过跟它对话,可能硬件已经变化了,但是它里面的那个数字生命还是它。
我的孙子跟他对话可以了解到某年某月某日它跟这个爷爷之间的关系,它是可以保存到这个程度的。
而且你如果仔细观察,现在的AI陪伴类的软件产品,真正能收上费的只有两项:一个是对话时长,第二个就是场景记忆。
场景记忆功能让用户的付费意愿变得非常高。
郝博阳:保存到具体的年月日的这样的数据?
孙兆治:对,因为它每天会在写日记的。
它有一个小功能,每天会写一篇日记。你可以通过APP来查看它的日记,它是对时间轴有非常清晰的认知。
郝博阳:它每天会记录什么?
孙兆治:这个问题很好,我到底该记什么?不该记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是交给模型来判断的。
而模型判断它的逻辑是说它是在作为一个你的情感陪伴的伙伴,以这个东西为准绳去判断这个事情。
我们不会去存储原始的用户的对话的数据,我们会即用即丢,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到模型,让模型判断这个东西总结出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就丢掉了。
8
基模会吃掉工具
但情绪价值的市场永远离散
郝博阳:你对这个产品的定义也是AI潮玩。那你觉得这个产品是更偏向于陪伴,还是更偏向于潮玩?
孙兆治:首先它一定是一个cross over的状态,现在我们也没有完全去定义它到底是个啥,它是个新的东西。一定要找一个词的话,我们把它叫AI搭子,就这是一个新的品类。
AI搭子将来一定会是一个品类,而且是一个挺大的品类。
郝博阳:就是非强功能性AI。
孙兆治:对,你想象一下,我们看的所有的关于科幻片或者是一些游戏小说里面,它里面总会有这样一个小机器人的角色,就是一个小跟班,它也没什么大用,主要是提供情绪价值。
可能有一点小用,然后这个整个电影结束之后,周边卖得最好的就是这个品类。
我们认为将来哪怕是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遍布世界每个角落的时候,这个品类依然是一个非常强力的品类,几乎每一个人都想要至少一个这样的搭子。
郝博阳:它不是解决问题,它只是解决情绪。以后机器人会是统一的形态吗?
孙兆治:它不一定是人形,这个小跟班不一定是个人形。因为它是个纯提供情绪价值的产品,所以它是遵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样的逻辑的。
如果它是一个生产力价值的东西,可能它会有唯一解,有可能出现赢家通吃的格局。但是情绪价值的产品,我认为它最终是一个离散市场,它会存在很多风格,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品牌,它都可以存活。
我们看到所有的偏情绪化场景的硬件的产品都是非常离散的市场。
郝博阳: AI陪伴APP类的产品,我们现在看来他们大部分最终都导向了一个恋爱关系。
孙兆治:对,或者是偏类人际关系,或者是这样一种感觉。
但我们是认为人和智能体之间很显然有其他的关系可以成立的,可以存在的。比如一个偏宠物或者说这种心灵互相支持的这样的角色。
9
第一代AI产品,不要靠AI讲故事
郝博阳:做第一代AI产品,AI功能和设计,哪一方面更重要?
孙兆治:这代产品来说,我认为设计更重要。
我们很多用户看到这个产品,直接会跟我们说,你这个产品就算没有AI我也想买。
一个这么可爱的毛绒的,眨巴眨巴眼睛的包挂足以让消费者动心,从卖货的逻辑上来说,颜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今天做好了心理准备,我们不要依靠讲AI的故事去吸引用户下单购买。
我们让这个产品本身很多方面就已经足够吸引用户了,等到用户用起来之后,可能AI的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才慢慢开始。
做AI硬件类产品的创业公司一定要有这样的觉悟,你很难靠讲AI的故事来吸引用户的。
像小米的AI眼镜现在也很火,它本质上卖的就是第一人称视角的拍照,大家要的是这个东西。
从用户视角来说,我看的是说它能够给我提供什么价值。AI的价值是非常难理解的,至少你没有深度的体验之前,它是非常难理解的。
就像一开始做汽车做自动驾驶的时候,不要期待说所谓的智能驾驶对于用户购车判断上面的吸引力足够高。
用户买车还是价格、颜值、品牌、舒适度等等这些东西。
但是用户开始用你的车之后,你如果自动驾驶做得好,慢慢用户会get到这个点。
10
泡泡玛特开了个好头
做toC产品得没有短板
郝博阳:朱啸虎据说是十分钟之内就决定了要投这个事。你觉得哪一个点是最让他能下这个决定的?
孙兆治:我觉得朱啸虎老师他首先肯定是想好了这个方向是好的,然后才开始找这个赛道的团队。
找到我们之后聊完之后是想听我对这个产品的一些理解,包括我们的核心的一些卖点是什么?我们做的减法是什么?我们保留的东西为什么保留?
聊下来之后他就觉得,你这个想法跟我的想法很像,而且可能有一些想法比我想的还要更细腻。
这个阶段无非就看两个,一个就是整个的创业的方向,再一个就是团队,看一下这帮人靠谱好就投了,决策非常的快。
郝博阳:市场上是基于什么判断认为这个赛道已经到了爆发点?为什么是现在不是去年或者是明年?
孙兆治:我觉得这个跟一个事件很有关联,就是去年底DeepSeek的爆发。
在去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讲说这个让用户跟一个智能体交朋友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他觉得模型能力还不到。DeepSeek至少让很多投资机构认为模型到了这个阶段了,它可以做这个事情了。
肯定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说去年的时候,泡泡玛特的股价还没涨这么厉害,那时候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情绪价值持怀疑态度比较多。
郝博阳:现在它的供应链是成熟的状态吗?
孙兆治:这类产品的供应链是相对比较成熟的。
现在你可以找到一些几乎是所谓的通版方案,但是通版方案可能做没有我们这个好。它基本上只能实现一个对话的非常简单的对话功能,就是一个对话盒子塞到一个毛绒玩具里面。
对话盒子现在华强北已经卷到可能二三十块钱一个,贴着成本在做。但是这样的产品解决方案,它的体验是很难做到很细腻的。
它的情绪怎么变化?它的性格怎么变化?然后我跟它很多的交互,能不能告诉大模型能不能知道这些交互能不能有长期的记忆等等,这些是很难做到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在这个赛道上基本上是两类玩家,一类就是选一个通版方案,另外一类就是像我们选了一条更难的路线,我们自研的模型,自研的长期记忆,然后我们整个硬件上面为了达到我们想要的状态,它完全没有办法用任何的现成的解决方案来做。
最终我们认为这群用户是一个体验敏感性用户,她不差这一两百块钱,她要一个好东西。
郝博阳:品牌叙事打算怎么去讲?
孙兆治:品牌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得长时间做。我们会去跟大家去讲述毛毛星球上面的金木水火土毛崽们的故事,我们会去构建整个的故事系统,整个的世界观。
同时我们很少有同类产品,从一开始就有线下体验店。我们会在7月份整个会有北京、上海、深圳三家线下体验店,大家可以去实际的,因为这个产品是需要上手的,实际地去体验它,去通过我们的店员去讲述这个产品的诸多的玩法,来一点一点地把这个品牌叙事给构建起来。
| 本节目也有音频 |

你可以通过腾讯新闻、小宇宙等平台收听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赞支持,或者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认识我们|
《Hao好聊》是由腾讯科技发起的深度访谈项目。我们关注那些正在重塑时代的人——他们是第一批触摸未来的人,在技术变革的浪尖上冲浪;也是搅动潮水的创造者,用代码与远见重新定义商业与文明的边界。
我们聚焦科技领域的「先行者」,与他们展开沉浸式长访谈,探寻技术浪潮下的思想交锋。当AI开始改写人类社会的底层逻辑,亲历者如何理解这场变革?当技术奇点临近,那些最接近答案的人,如何看待我们共同的未来 ?
《Hao好聊》希望深入技术狂热背后的人文思考,记录产业剧变中的个体抉择,与行业参与者共同探索未来的可能性,成为产业进化的见证者。
文章来自于微信公众号“腾讯科技”,作者是“博阳”。